
戈壁花开 发表于 2015-9-1
8月15日,领队李鑫带我们走进未知甘南。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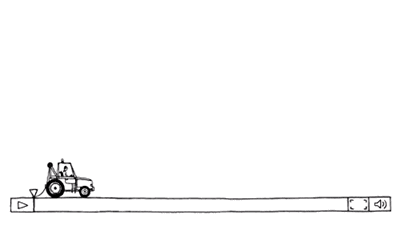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安多故事
安多藏区,三大藏区之一,与康巴和卫藏并列。其范围包括甘肃的甘南、天祝,四川的阿坝,西藏那曲的一部分以及除玉树以外的整个青海。概括来说,就是青藏高原东北一隅。藏族俗语说,马域安多。的确,安多正是一片连绵上千公里的草原,安多的文化正是豪放大气的马背文化。就连我们这些过路的人,也沾染了一份天地辽阔之气,纷纷敞开幽闭已久的胸怀,任由阔别经年的感动一次次席卷而来。
这是一片何等壮阔的草原:我们一路从兰州进入甘南,向南又进入阿坝,再向西直到青海东南部的年宝玉则。九天的时间里,走过积石山,迭山、西倾山,直到巴颜喀拉;跨过黄河、大夏河、碌曲、白龙江以及黑河、白河、无数无名的小河,光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就翻了好多次——这不过是安多的东南一角。
这是一片何等丰富的草原:草原中散落着神秘的森林和庄严的巨石,有牧人的家园和他们的牛羊。草地有红的,有黄的,有蓝的,有紫的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绿色。这里有三种白:牧人的帐篷,湖水中的白云和山头的积雪。这里也有三种红:喇嘛的僧衣,跳跃的篝火和夕阳下的悬崖。
我说不尽,更写不尽我见到的安多。我只见了区区一面的管窥蠡测的安多。我只是一个过客,穿行在穿红袍的喇嘛、虔诚朝拜的老人、自由奔跑的孩子和马背上的汉子之间,听着陌生的异域的语言,睁大好奇的眼睛,感觉草原上的风荡涤过风马旗和我的内心,教给我纯粹的快乐与感动。
我心中满是思念。
我又能写下什么呢?言语总是苍白无力,当面对刻骨铭心的记忆时。
我所能做的,只有讲几个安多的故事给你听,或许它是主角、或许它是舞台,有的七零八碎,有的寡淡无味,可是那就是我知道的安多,绝非虚构的安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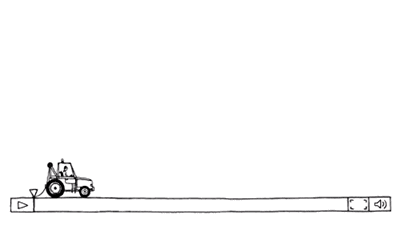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青铜牦牛、白塔和月亮
我在行程的第一天见到它,在兰州的博物馆。一头青铜牦牛,出土于同属于安多的天祝。它很萌,鼓起大眼睛看着来往的参观者。它也很逼真,牛角、牛头、所有肌肉……除了尾巴。尾巴是猕猴桃的形状,圆嘟嘟的纺锤形,夸张的毛蓬松着。
后来我特意观察,才发现牦牛尾巴的确是猕猴桃形的。草原上,四处游荡着我研究的对象。
牦牛不仅有夸张的尾巴,还有夸张的毛发。我要说的不是它们有多长,因为大家都在纪录片中见过它们垂到地面的长毛。我要说的是图案。我一路上见过上千只牦牛,有白尾巴,有白腿,有白肚子。最浮夸的是白脸。某些牛喜欢把脸长成白色,还留下黑眼圈和黑鼻头,简直就像骷髅,几次吓我一跳。某些牛从头到尾沿脊梁骨一条白道,让人不禁想起玄武岩中的石英矿脉。某些牛,干脆就是石头,全身白色,略带暗斑,酷似路边一块巨石。
那头牛还脾气不小,或许是拜花色所赐。它吃草的地方不许其它牛闯入。我亲眼见到一头靠近它的小黑牛被它甩着长角赶跑。那一天,还有三个喇嘛逗牛玩,结果被怒气冲冲的牦牛赶上山坡。我说过,喇嘛的僧袍是红色的。
这起冲突让我们在横穿群牛阵时平添了几分谨慎。我迈一步,它退一步,半分钟过去了。我又迈一步,它又退一步,半分钟又过去了……就是这样,直到那头牛老大不情愿地让开灌丛中只容一人过的小径。我默默地走过去,小路两边,山上吃草的,湖里洗澡的,好奇地看我一眼,又嫌弃地掉转回脑袋。
牛,才是这里的主人(隔壁的羊不要冲动,你们也是……)。而我,只是过客。
公路上溜达着去上班的,山坡上辛勤工作的,酸奶盒子上做代言人的,全是牦牛。而且,它们都腰缠万贯。
一头牦牛一万五。
同行的朋友说了个故事。她有个青海的大学同学,每学期都说她家又卖了头牦牛供她读书,同学们都同情她,每年都捐款。毕业时,大家问,你家有多少牛啊,怎么还没卖完?青海同学说,也就五百多头吧。
所以藏民要为牦牛立雕像,比如博物馆里那头。
第二天,我们要穿过两个自治州。一个是黄土高坡上的临夏回族自治州,一个是世界屋脊的边边上的甘南藏族自治州。两州交界处不甚明显,都在大夏河边,东边爱吃牛羊肉的县叫临夏,西边牛羊漫山跑的县叫夏河。
在那一带河谷里,每个村镇有两座高大的建筑。一座是顶着金色小月亮的清真寺,另一座是藏传佛教寺庙的白塔。
无论哪一边,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:虔诚。
因为信仰,每一个顽强生存在黄土坡上的村庄都会建起富丽堂皇的清真寺。是的,每一个。从公路上放眼望去,山坡上,河谷里,到处是金色的小月亮。
因为信仰,回民在河水中洗澡时,只有白帽子不会摘掉;因为信仰,草原上赶路的司机会把车停在路边,铺开毯子,几个人双膝跪地、双手摊开、朝西祷告。
在郎木寺镇上,几乎所有餐厅都是丽江阳朔风格,贴满了背包客的留言和文艺气息十足的装饰。暖黄的灯光一打,昏暗的木屋充满了暧昧的感觉。只有阿里餐厅不同。
餐厅一色白墙,整洁干净,还有禁止喝酒的提示。最醒目的地方,写着: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阿拉是主的使者。
出门在外时,如果不知道去哪里吃饭,找一家清真餐厅是没错的。虽然不一定口味够重,但是干净卫生有充足保证。
可以说说白塔的故事了。
藏族的白塔有八种,或多或少与死亡相关。其中一种叫做“牙塔”。
在藏区,尤其是去布达拉宫的路上,经常会见到磕长头的朝拜者。在寺庙,比如拉卜楞寺或郎木寺,我也见到了不少在大殿或佛塔前五体投地的信徒。还有转山转水转佛塔的、在转经廊里推动经筒的……各式各样的朝圣者。而藏区的自然又是如此严苛,六月飞雪不稀奇,百里无人烟也是寻常。当过路的藏民见到这些衣衫褴褛的虔诚者,一定会施舍水和干粮。当磕长头的人见到同行者的尸首,会敲下一颗牙,装在口袋里,等朝拜完成后带回家乡,修一座白塔将一路收集的牙齿供奉。
一位藏民可能穷其一生的积蓄修一座白塔。一片草原上的藏民可能集全体之力修一片塔林。
瓦切塔林修建在十世班禅曾经讲经的地方。其中的菩提塔最大,上百个小佛塔组成金字塔形,最顶上则是镀金的主塔。每个小塔都供着不同的佛,每个小塔上都是一幅精美的壁画。其中一头狮子,要画一个月。这种壁画和唐卡有些类似,都是藏民表达信仰的途径。颜料都是由矿物加草药制成,画师每画一笔都要念一遍六字真言,让一幅画一经完成就带有灵气。
瓦切塔林不大,就在公路边,要收门票,不过这些门票的钱被用来修建一所唐卡学院。那也是一座更大的白色建筑,离班禅讲经地那座塔不算远。施工的藏民坐在土坡上休息,一旁的转经廊下野花盛开。诵经声里,几个老人推动上足了油的经筒,金属的、木制的,新的旧的,一圈圈的六字真言在空中流转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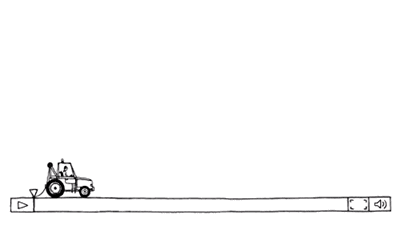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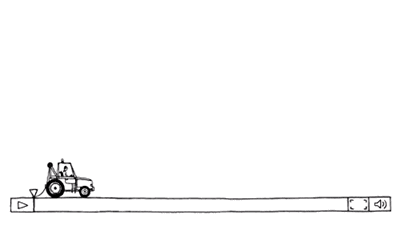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喇嘛别闹
格尔底寺(就是四川郎木寺)的小喇嘛管我们的领队叫“胖子”。刚到时,他们正在草甸上打羽毛球,见到胖子后一路欢呼着冲过来。一个红色冲锋衣的大个子,一个红色僧袍的小不点,两个拳头一撞,就算是欢迎。小不点抢过大个子的旗子,挥舞着向他的小伙伴们跑去。
没错,这就是传说中的喇嘛。
我来安多之前,和大多数人一样,以为喇嘛很神秘,至少很严肃。以为他们就像内地寺庙里的和尚一样,不苟言笑,一心念佛。虽然我早该从《聪明的一休》、《三个和尚》和《乌龙院》中看出宗教逗比的一面,但是内地的僧人严肃得让我不敢想太多。
在夏河的拉卜楞寺,我小心翼翼地问一个青年喇嘛,可不可以给他照相。喇嘛挠挠头说,照我干什么,然后露出一个腼腆羞涩的微笑。
从那以后,我就开始不停地见到喇嘛,和他们交谈,和他们玩耍,并且逐渐意识到拍一张喇嘛的照片绝不是什么丰功伟绩。然而我还是拍个不停,只为了扭转自己和其他人对喇嘛的印象。
索克藏寺的山坡上,出现了两个穿红色僧袍的身影。二人面对面站立,一人面对山下的黄河九曲第一湾,另一人面对着他。
看,他们在互拍,一个用手机,一个用平板电脑。游人们惊呆了,纷纷驻足围观。然后,他们钻过铁丝网,来到我们这边,继续游览。我在山坡上架好三脚架坐等日落,两个喇嘛也来到我身边,主动开始了亲切友好的交谈。
你从哪里来?
我是北京的。
哦对对对,北京去过的,北京哪里的?
您去过鸟巢吗?我家在鸟巢旁边。
哦对对对,鸟巢去过的。他们也是北京的吗?(指我身旁众人)
他们是深圳的。
哦对对对,深圳去过的。
您还去过深圳?
深圳、香港、珠海、澳门,都去过的。
……
这位可爱的大喇嘛四五十岁年纪,有一张大圆脸盘,慈祥而亲切,手里捻动着佛珠和手机。
他是甘南合作市的喇嘛,家乡在我们刚刚去过的世外桃源扎尕那,这次出来旅游到了四川唐克的黄河边,旁边坐着的是山下索克藏寺的喇嘛,算是陪同他游玩并提供逃票路线的。离别前,我用他的手机给二位合了张影,说有缘再见。其实他给我看过他们寺庙的照片——在手机上——并且报上了一个四个字的拗口的名字,当天晚上,我就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。真的是有缘才能再见了。
一路穿州过县走草原,大大小小的喇嘛见了无数。成群结队下河戏水的喇嘛,骑着摩托赶路的喇嘛,在草地上野餐的喇嘛,逗牦牛玩被赶跑的喇嘛……
我不禁想为他们唱首歌:
咱出家的人,有啥不一样,只因为我们都穿着红色的僧袍……
格尔登寺的晚课开始了(注意不是小喇嘛玩耍的格尔底寺,一会儿我们还要切换场景),半大不小的喇嘛三五成群地向大殿走去。还没有全部坐定,诵经声已经响起,如果让我形容的话,就是中小学的早读。有人卖力大声背诵,有人头抵在柱子后面酣睡,有人好奇地看着外面的游客。有些句子读得深沉,有些句子读得激昂,有些句子读着读着,两个喇嘛一对视就开始偷笑。一个段落读到结尾会有一个音格外长,像咏叹调一样,或是干脆就是一声长叹,余音袅袅,不绝如缕。然后下一个段落又开始。像合唱一样的和谐感,像唐诗一样的韵律感,虽然听不懂藏语,但是我如痴如醉。
更值得一看的是格尔底寺的辩经。晚课七点结束,只听得殿内诵经声罢,一声整齐的欢呼或者说是狂啸,大大小小的喇嘛飞奔出殿,一阵追跑打闹过后,辩经开始。
一排坐着,一排站着,站的提问,坐的回答。可是没那么沉闷,确切的说,实在是欢乐。提问者的标准动作如下:左臂伸直,右手沿左臂上捋,高举过头顶,后退一步,右手落下,左手回缩,两掌一击,前进一步并跺地,右臂伸直,指向对方,再进一步,大声提问!
现场一片混乱,击掌声,争吵声响成一团,喇嘛个个表情狰狞。带着黄色大帽子的高级喇嘛像教导主任一样,四处巡视并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寺院就是学校,和公立学校一样教授藏汉英三种语言,只不过主课不是数理化,而是经文。孩子们五六岁被送来,七天回一次家,从小学读到博士。能背诵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两部经书共一百三十万字者可以考取小道格西(教授),能背诵五部经书的就是大道格西,成为某一片藏区中受人景仰的德高望重的学者。瓦切塔林的讲解员说过整个川西只有一位,住的不远,就在草原上,你们有空可以找他聊聊天——而且他治结石很有一手。
所以我的结论是:天下的学校都是一样的,有认真的,就有淘气的,有人抱着课本背书,有人混在小卖部,想深造有布达拉宫可以去,想毕业也很好找工作。
小喇嘛开始玩篮球了。胖子接球,他们喊。清澈的欢笑让我们几个大男孩、老男孩都跃跃欲试。加一个,我们喊,于是,一场有纪念意义的游戏开始了。地点是格尔底寺后大草甸离白龙江源头五百米海拔三千四;时间是夕阳西下红石崖格外鲜艳寺院金顶闪亮光;人物是五六岁到不惑之年藏汉两族混搭队。起因是胖子带头;经过是玩得很爽;结果是高原不宜剧烈运动感觉有如圆明园跑完三千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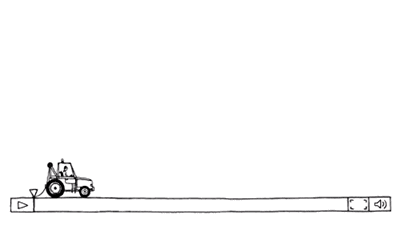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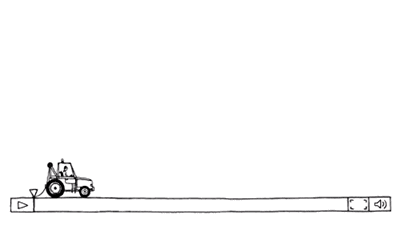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姐姐弟弟
我从三年前开始几乎不跟旅行团玩到现在,这次又一次跟了团,原因自然是这个团不一般。三餐里只管早餐、到了郎木寺这种美食天堂连早餐也不管了;一路慢节奏,比如扎尕那,别的团停留三个小时,我们是一天一夜;一路同行都是同道中人,爱风光爱西部、起早贪黑找光线、吃苦耐劳闯四方。总结就是约伴一起自由行,酒店有人订好了,并且,交通费省了一大笔。
一起打马过草原的同路人中,年龄跨度将近五十岁,并且来自天南地北。有人背着长枪短炮胶片数码一路快门像机关枪,也有人一路睡觉,有人独自一人去找角度把照片发群里引来一片惊呼,也有人,拉帮结伙只为了肚子。
我属于拉帮结伙的,帮派里除了我妈和另外一对特别会吃的北京夫妇以外,全都是九五后——没错,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的人,零零后、小胖子,我们所有人叫他弟弟(竟然如此浅显……)。还有三个上大学的姐姐,看起来最小的就是弟弟的亲姐姐,另外两个是她同学。虽然她们也叫我弟弟,但是从现在开始,只要我的文字里出现弟弟,一定就是那个车上一路睡觉的、比我还小三岁的帮派最神秘成员。
在扎尕那,又冷又饿的我和我妈遇到了又冷又饿的姐姐弟弟,一起奔向当时我们眼中百里迭山最亮的星,深夜还有饭吃的,大拇指客栈。那天晚上,一小碗糌粑,姐姐一人一口,剩下的归我(大概是寒酸而珍贵的四五口),让我好生感动。
第二天出山,到了领队反复吹嘘的繁华的大都市,迭部县城,我们相约去吃藏香猪(默默吐槽我们住的就是藏香大酒店,地方特产可见一斑)。走进饭店,遇到了帮派未来的两位核心成员,二位也是一阵惊喜——来来来,一起吃好点菜,每样都能尝到。服务员!一斤白灼的一斤红烧的,再来一斤手把肉!
从此我们结缘,从甘肃的地盘吃到四川的地盘,一路吃过唐克的黄河鱼,红原的炮仗面和泡馍,阿坝的串串、木桶鸡、木桶鱼,郎木寺的牛肉汉堡、酸奶、米线,一直到合作的手把肉。
八个人好算账,分一半他们出再分一半我们两家出。到最后已经成了习惯。同样成为习惯的还有太多别的,直接导致最后一天回到兰州分开后,我和我妈都恍恍惚惚不会吃饭了,找了家又贵又难吃的店,一晚上各种不顺。
我和弟弟永远霸占最后一排。我一路拍照,看中最后一排能开窗户,弟弟一路酣睡,很高兴他可以占两个座位。过巴颜喀拉时,弟弟那边雪山晨雾美如画,我腆着脸摇晃他,哥们儿醒醒,咱换个座位好不好?拍完以后,公路一转,风景到了另一边,弟弟又睡着了,我却没好意思晃醒他。在郎木寺的第一天下午,我们商量第二天要不要去看日出,姐姐提供了一条一句顶一万句的理由:弟弟要去。搞定。在整个行程的最后一个早晨,弟弟终于丢失了睡眠,为了郎木寺的日出,很美很清澈的一个日出。
弟弟可喜欢跟着我混了,他似乎等不及总是各种照相的姐姐们,一个人穿着灰色的帽衫,帽檐遮住眼睛,默默跟在我身后,像一个萌萌的圆圆的大大的多多洛。在年宝玉则,弟弟跟我走导致姐姐找不到他,给妈妈打电话,被骂了,说你怎么把弟弟弄丢了。那时弟弟在湖边淡定地和我们一起吃野餐,我们说,弟弟啊,吃的都在你这里,雨伞也在你这里,祈祷下雨吧,看姐姐们不来找你怎么办。
后来,年宝玉则山顶乌云骤起,一阵雨夹雪带冰雹的奇特天气扑面而来。姐姐那时已经找到了弟弟,却没有人打伞。那是这四个深圳的孩子第一次见到雪落在身上的样子。
弟弟爱吃猪肉,对其他肉兴趣不大。在阿坝的第二个晚上,我们点了木桶鸡和木桶鱼,了解到真相后我们又去超市买来午餐肉放进汤里涮,弟弟可劲地吃。之前几天,总觉得弟弟不太爱吃饭,于是我放心地做了一个嚣张的吃货。那天,我看弟弟吃起猪肉来那么幸福的表情,真的不好意思和他抢了,老老实实地啃自己碗里的鸡爪子。也许,弟弟真的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。在郎木寺吃饭时,总是小心翼翼地慢慢吃,等下一盘菜上来,大家喜新厌旧地哄抢热乎乎的肉时,才动筷子吃上一个盘子里省下的几大块肉。三个姐姐,一个没骑过马,无辜地站在马屁股后面,被踢了;一个没上过高原,在迭部才买厚裤子;还有一个爬上石头照相都能把脚磕破了。总之,我认为弟弟是一个有着无比智慧又低调如谜的男人。
我们去阿坝时路过一座漂亮的藏寨,我看天色尚早,号召大家打车回去看看。当时应者如云,最后一看风雨将至,又都说不去了。当我和我妈执著而孤独地坐车到寨子口,沿小路向对面山上走去,汽车声从背后响起。一回头,只见一辆面的上塞着六个人,弟弟坐副驾驶座,没有睡,看着我们笑。上车挤着!
车爬上山后云开日出,对面村庄宛如仙境,帮派里的三台单反响个不停。
那天晚上,我们到格尔登寺听晚课,听到半截,姐姐发现了一个超可爱的小喇嘛,我们一路小跑跟上并威逼利诱,希望得到玉照一张,结果被熊孩子遛得团团转,一举起相机他就躲,收起相机他就探出脑袋逗我们,笑容无比灿烂。气急败坏之下,我们一起去吃了顿串串,八个人二百八十四串,肚子溜圆回去睡觉。
离别前,郎木寺的早饭,白族人开的米线馆子。三个姐姐吃四碗,我和弟弟吃三碗。
留言纸上,陆续出现了以下字迹:好冷。米线好热,好好吃。好想再来一碗。已经实现了。加辣椒花生米味道更佳。
临走时用一根牙签,把我们的留言别在前辈的上面。以此纪念五个九五后吃货曾经来过。
在兰州的大街上,匆匆忙忙跳下汽车,有人奔向火车站,有人奔向飞机场,有人奔向下一个出发,有人回家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。还没有认真告别,就只剩一个背影。只因为告别不敢太长,太长了,容易压不住奔涌而出的泪。相伴千里,却不知何日再相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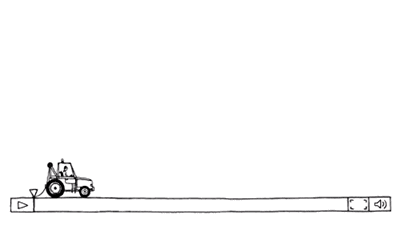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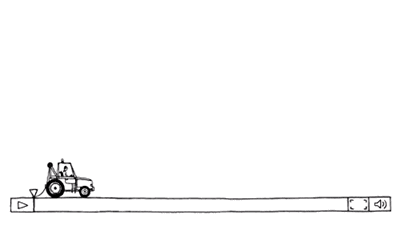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萍水相逢
扎尕那的峡谷里,小雨初歇,我和我妈在藏民留下的火堆旁奋力吹起了火苗,放上饼子烤热,顺便烤烤自己。远方走来四个游客,两个妈妈带两个孩子,驻足围观我们诡异的取暖方式。一块休息一下吧,挺暖和的,我们招呼道。于是,她们也加入了这个原始人部落,愉快地烤起了火。火苗跳动着,一根长长的树枝捅进去,烧着的那段成了灰白的炭。把手伸到火边,六双,看不见的对方表情,但是谁都没有挪窝。板砖一样的的饼子烤过后一面焦黑,掰下来扔进火堆里,剩下的像面包一样松软和温热,就着一杯从碌曲草原买来背到这里的酸奶,我只想说,生活静好,岁月如诗。上次我说这句话,是我们的微电影,说的是吃着灌饼等公交的人。这一次,我没想到,这一群吃着饼子烤火堆的人竟然也是诗意青睐的对象。
神奇的是,从那以后,在景区门口,在唐克的小饭馆、阿坝的小吃店,在年宝玉则雪山脚下,我们一次又一次相遇。我们从兰州进兰州出,她们从成都进成都出,仅有的几次交汇都成为交集,只能说是缘分使然。当然最后的交集随着我们离兰州越来越近而越来越远,唯有在回忆起时,再道一声珍重。
还有那些一起踢球的藏族少年。我们在四千米的草原上奔跑,雪山圣湖作舞台,蓝天白云作背景。踢的是在北京都不屑于用的最破的足球,参赛队员有的穿着藏袍,有的穿着马靴,一片灵异的气氛。他们说,你们汉族会高反,不让我去捡球,然而我还是很积极地跑动,回去的路上果然大腿抽筋头晕气短,吃完整整一板巧克力才宣告康复。
说到巧克力,我又不得不提那条唐克的小狗。最开始,我相中的模特是趴在山坡上看黄河的一条小白狗,后来,它的身边又多了一条黄腿的小黑狗。我羡慕了它们一会儿,就去跟喇嘛侃大山同时拍拍黄河第一湾的全景了。拍摄行将结束,也送走了喇嘛,我找到姐姐弟弟——应该是要商量晚饭的事了不过我已经饿了——问问有谁带了吃的。我接过一块小面包的同时就看到它,从山上跑来,兴奋得不能自已。小黑狗,它围着我直打转。我们商量了一下,决定采取绥靖政策,我把面包扔到地上,然后任由它沿着山坡向下滚。小黑狗也飞快地跑。等到面包滚到草丛里停下来,小黑狗也一个急刹车。在我们的注视下,这家伙竟然挑食了。它咬了一口之后,嫌弃地丢下面包,又欢脱地跑回来。
我们这次统一了手势,摇着头,摊开双手,没有没有,真心没有。小黑狗失望地低下了头。我们又说起巧克力,我说我好像带了巧克力。姐姐们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依然粘着我的小黑狗。我说狗吃巧克力拉肚子……说时迟,那时快,地上趴着的那位充满期待地抬起了脑袋。
摇摇头,摊开双手,没有没有,真心没有。
我们走的时候还议论着它,这小子饿不坏,旁边有个索克藏寺,可爱可敬的喇嘛们一定会发慈悲的。
估摸着小狗也吃饱了的时候,我们在唐克吃黄河鱼。夜里八点,厅堂里只有一个腼腆的四川小伙子帮我们点菜。领队说过,草原上素菜比肉菜金贵,又实惠又好吃的就是红军野菜,八十年前人们走过这里时的主食。我们问,有没有红军野菜?他说没有。下一句就是,我去对面那家问问。那天晚上,我们吃到了地道四川风格的放了香油辣椒的红军野菜。
我们还有一个白兰瓜,从兰州背到夏河、到扎尕那、又到了唐克,一路香气从行李架上飘来,馋了我妈三四天。直到这里,我们才找到了吃瓜的理由:八个人凑齐,并且就我们一伙食客不用管太多规矩。老板娘看到瓜,说,我们里面有菜刀。下到厨房里,正切菜的小伙子放下手里的活,捞一盆黄河水,把瓜丢进去滚了一圈,放在案板上,一切四瓣。加上北京的叔叔还有我,两个人掏籽一个人切,八斤沉的黄灿灿的果肉放在人家用来装酸菜鱼的盆里就端上了桌。然后再五分钟后消失殆尽。遗憾是没有想到给饭店里忙着帮我们做菜的几位尝一尝,或许一声真挚的感谢也不算太轻。
所有的汉子、妹子,可爱的藏族孩子,大喇嘛和小喇嘛、各种牦牛、各种狗、天上的云、地下的草。萍水相逢的所有所有,再见了,祝你们万事胜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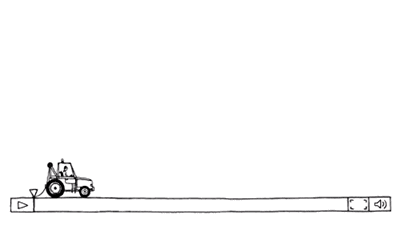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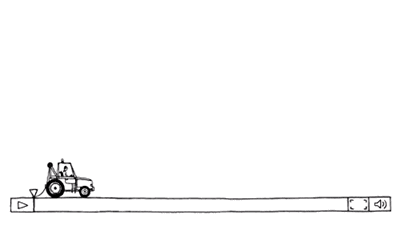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牵挂
原谅我讲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,是时候做个总结了。
在仙女湖边,同行的摄影师问我们,为什么还要回家?回去以后,吃的有毒,喝的有毒,呼吸的空气都有毒。在这里,买几头牦牛就能过得很幸福。
有人说,家里新装修的房子还没住呢,有人无语凝噎,我说我们开学要考试了,我还有不到一周复习,然后觉得理由好苍白无力。
摄影师喝一口啤酒,就着蓝天,大声宣告:就是因为牵挂!所有的,都是为了牵挂。
牵挂,是个很好的答案,不仅是回家的理由,而且是出门的理由。
我牵挂的是一本书中那匹若尔盖的小狼,所以要来看看草原是否安好。我也牵挂无数传说中淳朴善良的人,所以要来看看他们的笑容有多么纯真。我曾在报纸杂志上读到过度放牧和荒漠化,来到这里,我看到标语上写着:留住湿地就是留住我们的未来,保护高原湖泊就像保护我们的眼睛。有的草场牛羊成群,但还有草畜平衡区里野花安然开放。每当我看到经筒有人转动,听到六字真言在耳边响起,心中就是一片安宁。
我来了,为了牵挂。我走了,带去更多牵挂。我忘不了所有的风景和所有的笑脸,我会为他们在远方祈祷。我感激安多带给我的快乐,我也祝愿它一切安好。祝愿它的马儿和雄鹰自由依旧,祝愿它的牛儿和小狗永远幸福。喇嘛们,好好念经,天天向上,也许未来会有一位活佛说他跟一个北京孩子玩耍过。
我越来越想念我的安多,留给我几缕遥远的故事又让我牵挂的安多。但我只有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。
有一首很好听很好听自从我回到北京就一直听的歌,叫作,一个西藏。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,大家把西藏两个字,默默理解成安多就好。
一座高原
一个西藏
十万边疆
五百山水
三千佛唱
四封短信里坐着我
大雪围困的凄楚故乡
两扇庙门
六个磨坊
九个远方
谁是第十一位面色潮红的酥油女王
然后鹰飞
然后草长
并且青天在上
心日朗朗
白牦牛的犄角
究竟为何它又弯又长
我向天堂
住在你心上
有三分幸福
有七分迷茫
四个牧民
三个喇嘛
两个铁匠
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
我和世界只有一个安多。
THE EN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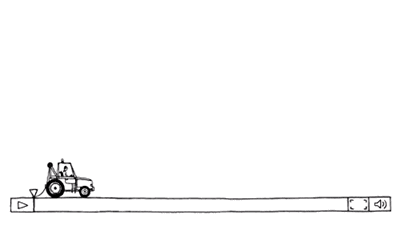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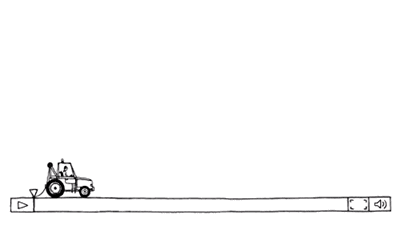
2018-10-23 13:37:25